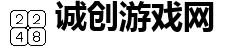夜色像一张厚重的毯子,压在黑色的天窗上。我踏进废弃诊所,金属门的吱呀像哭声,走廊的灯泡仅有残留的微光。墙上斑驳,药柜的玻璃碎裂成星点,空气里混着霉味与消毒液的余温。地板潮湿,脚步发出回声,我的呼吸在口腔里打着冷颤。转角处的日历久远得像一块枯骨,指针指着一个没有日期的日子。
我在尘埃里翻出一只铁盒,盒盖上粘着时间的灰尘,里面是一盘黑色的录像带。盒末写着几个字,像自我之外的秘密:请勿打开。我并不怕,像闯进一座被遗忘的剧院,灯光依旧在舞台上晃动。我把录像带接入老旧的摄像机,屏幕跳出雪花,声音里有空洞的呼吸。画面里是一个手术室,金属桌闪着冷光,墙角的时钟滴答着,像在数着某种不可见的时间。
镜头忽然切换,出现一个看不清脸的医生,口中念着某种代码,旁白像是对着内部记录。带子里的人被束缚,椅子上有一道道鲜明的铁痕,墙上贴着编号的标签。一个女孩的名字被涂改成新的字样,但我从指纹和发黄的笔记中认出那是我的家族名。画面时而模糊,时而清晰,我仿佛听见昔日母亲的回声,提醒我别靠近那扇被封死的门。

录影的结尾是一段快进的剪切,像是有人在赶着清除证据。下一幕出现了一个空着的病房,墙体的裂缝里藏着隐形的数字,像是要告诉谁隐瞒了什么。屏幕突然出现我的影子,甚至是童年的影像,仿佛录像带把我带回了一个被抹去的夜晚。月光透过窗棂,映出我手中那盘带子的暗红色末端,指针在时间上打着一个并不愉快的节拍。
我把带子塞回盒子,带着诊所的阴影走出门口。夜风把门缝吹得发颤,铁铃在远处摇响。也许真相永远刺痛,却像针脚般将我与过去缝合,无法完全拆散。我没有把它交给任何人,只把心事尚未说出口的部分留在胸腔,继续前行,直到新的一天把影子托到墙上,形成一个可以呼吸的轮廓。我将这份回忆折成纸船,塞回心底某个抽屉,愿它在夜里安睡不再翻涌,却也不被完全遗忘。若有一天遇见熟悉的笑,我会知道自己仍活着。